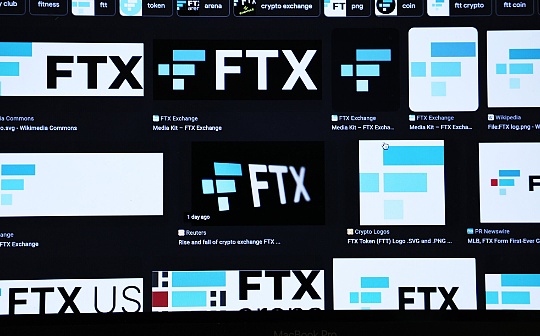NFT平台“洗售” or “欺诈”?一线之隔


核心提示:
1、数藏平台自买自卖的“洗售交易”行为,既有可能构成民事欺诈,又有可能构成刑事诈骗
2、目前数藏行业缺少针对性的监管规定,监管力度可能逐步收紧,我们强烈建议数藏平台摒弃洗售交易,同时限制平台员工对本平台数字藏品的自买自卖行为。
3、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分问题复杂多样,我们建议通过“重要事项+民事救济可能性丧失”的标准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充分发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洗售交易(Wash Sale)” 原本是证券、期货交易领域的名词,指行为人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进行自买自卖的行为, 行为人常通过自买自卖来制造股票、期货交易非常活跃的假象,从而误导投资者争相买入,以此拉高证券产品的价格 。
以证券、期货为对象的洗售交易为刑法所明令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明确规定,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 情节严重的,构成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 。在我国,通常将法定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称之为“重罪”,操纵证券、 期货市场罪的 最低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中的重罪 ,国家对于证券、期货市场中洗售交易行为的打击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部分数藏平台也存在典型的洗售交易行为。较为熟知的案例是前段时间网络黑客团体将国内某数藏平台自买自卖炒高价格的证据公之于众,进而引起该平台消费者的巨大恐慌;又如某平台通过自买自卖行为将平台发售价格仅百余元的数字藏品炒作至6000余元。
上述案例中自买自卖的洗售行为显然违反“三协会倡议”关于自觉抵制NFT投机操作行为的规定,但问题在于“三协会倡议”的性质仅是行业规范,由此必须追问, 数藏平台针对数字藏品的洗售行为,除了涉嫌违反行业规范外,是否涉嫌触犯刑法? 我们认为,数藏平台针对数字藏品的洗售行为具有构成诈骗罪的刑事风险,必须予以重视。

二、以数字藏品为对象的洗售交易的性质分析
(一)欺骗、民事欺诈与诈骗的关系
商品交易过程中的欺骗行为普遍存在。如商家为了将商品卖得好价钱,通常会在商品进价、商品功能等方面对消费者做以夸大, 这种夸大便是典型的商品交易过程中的欺骗行为 。类似的欺骗为法律所容许,亦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之现象。
在此基础上,某些行为的欺骗程度可能更重,以至于违反《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范,消费者可以根据上述法律规范寻求民事救济,这类民事欺骗行为学界通常称之为“ 欺诈 ”。
倘若某一欺诈行为除了违反《民法典》等民商事法律外,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则这类触犯刑法的欺诈行为便称之为“ 诈骗 ”。
因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欺骗、欺诈、诈骗三者的范围逐步缩小,欺骗行为的范围最大,毫无疑问所有的欺诈和诈骗都是欺骗行为。再考虑欺诈行为与诈骗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大致认为诈骗行为是欺诈行为的真子集,即 构成民事欺诈的行为,不一定构成诈骗 ;但诈骗行为一定也符合民事欺诈的特征。
(二)特定情形下以数字藏品为对象的洗售交易属于欺诈行为
欺诈有两种典型的行为模式,其一即 虚构事实 、其二即 隐瞒真相 。以数字藏品为对象的洗售交易,平台通过自买自卖来制造数字藏品市场活跃、数字藏品能够大幅度升值的假象, 这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 。倘若通过洗售使得该数字藏品的价格严重背离其原本价格,那么这种虚构事实的行为就已经不是为法律所容许的、商品交易中存在的欺骗行为,而是民事欺诈。消费者可以主张相应的民事救济,救济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主张《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所规定的撤销权。即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特定情形下,即平台通过洗售使得数字藏品的价格严重背离其原本价格的情形下,相关的洗售行为并非法所允许的欺骗行为,而是欺诈行为。下一步我们便要分析, 这种欺诈行为是否触犯刑法,进而具有构成诈骗罪的刑事风险 。必须承认,一直以来,如何在诸多的欺诈行为中筛选出刑事诈骗案件,对欺诈行为进行有效的刑民界分,是理论与实务中的难题。
(三)欺诈与诈骗的区分——现有学说之展开
在比较法领域,日本刑法学界的有力观点认为, 如果交易的对方知道真实情况便不会实施该财产的处分行为,却捏造这种重要事实,这样的行为就是触犯刑法的诈骗行为 。由此,日本早期判例认为,“即便冒称商品名称,而其品质、价格毫无变化,买主也并不拘泥于商品名称而是自己鉴别后买入的场合,并不构成诈骗罪。换言之, 当欺诈的内容对于买主处分财产的行为并不重要时,此种欺诈不可能构成刑事上的诈骗 。此即所谓的“ 重要事项说 ”。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实务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具有留日背景,“重要事项说”对我国刑法学界、实务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按照该说,欺骗行为是否实质性地侵害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成为刑事上的诈骗行为,应当取决于“ 作为交付之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 ”为标准。至于交付之判断基础的事实中的哪些内容是“重要事项”,一般认为“经济交易的重要目的能否达成”就是判断重要事项的标准。以数字藏品市场为例,不可否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购买者购买数字藏品是为了赚取其升值之后的差价。那么“ 赚取升值后的差价”就是购买者的“经济交易的重要目的 ”。在这一基础上,数藏平台通过洗售交易制造了数字藏品可以大幅度升值的假象,这一欺诈行为就是对于“重要事项”的欺诈,因而 具有构成刑事诈骗的法律危险 。

三、对刑事诈骗成立范围可能的限缩解释
不可否认的是,“重要事项说”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诈骗犯罪的处罚范围,即卖家对于“非重要事实”的欺骗,并不应为刑法所禁止。然而“重要事项说”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其一,“作为交付之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如何界定,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其二,某些民事欺诈的内容同样属于交易的重要事项时,应当如何对民事欺诈和诈骗进行区分?针对“重要事项说”的上述问题,国内学者对该学说做出了不同程度的修正。
(一)修正的重要事项说——以“民事救济可能的基本丧失”作为欺诈行为刑民界分的标准
有学者认为,在上述“重要事项说”的基础上,应当以“民事救济可能的基本丧失”作为欺诈行为刑民界分的标准。 该理论认为,民事欺诈和诈骗的区分关键在于“民事救济无力” 。举例而言,倘若被害人在交付财物后即便能够发现真相,也难以通过民事诉讼等救济措施弥补损失,则构成刑事诈骗;反之,虽然受害人在于给付相关的重要事项尚陷入认识错误,但只要采取相应的手段就能够保障财产权益,就属于民事欺诈行为。
具体到数字藏品领域,倘若数藏平台通过不断的洗售交易,造成数藏市场活跃的假象,从而误导消费者竞相买入,当该数字藏品的价格严重背离其原本价格时,数藏平台便构成民事欺诈。在这个基础上,倘若数藏平台 随时预备“卷款跑路” ,或提供 虚假的投诉、维权渠道,虚构平台信息 ,致使消费者在购买数字藏品后失去了民事救济的可能,那么此时平台的洗售交易行为便是典型的刑事诈骗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理论是合理的且能充分体现出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首先,该理论与目前我国司法实务的做法相契合。刑事审判参考第1342号指导性案例明确区分了陌生人之间的诈骗与熟人之间的诈骗,在陌生人诈骗的场合,由于被害人不知道犯罪分子的姓名、住址、犯罪分子一旦诈骗得逞,便会切断与被害人的联系,进而 使得被害人丧失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民事救济的可能,此时犯罪分子便构成诈骗罪 。这一裁判要旨与上文所列之数字藏品领域洗售交易在特定情形下构成诈骗罪的内核是一致的。其次,民事救济可能的基本丧失与诈骗罪中的“ 非法占有目的 ”之认定,属于一体两面之问题。二者属于同一对象的主客观两个方面,这亦能够与传统观点做到理论上的自洽。最后,该理论能够显著限缩刑事诈骗的成立范围,进而发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四、结论
(一)数藏平台“洗售交易”的红线界限
正如上文所述,数藏平台通过自买自卖的洗售交易,虚构数藏市场繁荣的假象,进而拉高数字藏品售价的行为,可能构成一般意义上的欺骗行为、民事欺诈行为、刑事诈骗行为。
1、当数藏平台 偶尔出现洗售交易 ,且对数字藏品的价格 影响极小 ,甚至并没有影响到数字藏品的价格时,这种情况 不宜认定为民事欺诈 ,而应当认为是商品交易过程中所容认的欺骗行为。
2、当数藏平台通过 频繁的洗售交易 ,制造数藏市场繁荣的假象,大幅拉升数字藏品的售价,使得数字藏品售价 严重背离其合理价格时 ,这种洗售交易便有可能 构成民事欺诈行为 。此时数藏平台不仅涉嫌违反“三协会倡议”,亦有可能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消费者可依据《民法典》主张相应的民事救济。
3、在第二种情况的基础上,倘若有证据证明数藏平台随时准备“ 卷款跑路 ”,或虚构平台信息、虚构联系方式、公司地址、投诉渠道等信息,则 该洗售交易行为便有极大的可能构成刑事诈骗 。
(二)数藏平台对待“洗售交易”务必要树立红线意识
上述“洗售交易”的红线界限仅仅是充分发挥刑法谦抑性原则基础上的结论。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数字藏品洗售交易行为的 刑民界分是具体的、动态的 。倘若数藏行业整体发展混乱,金融化趋势明显,势必会引起监管部门的强力监管,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鉴于此,我们在此强烈建议:
1、尽最大可能 避免平台员工买卖自己平台的数字藏品 ,以防止潜在的不受控的洗售行为;
2、 摒弃平台官方渠道的洗售交易行为 ,即使仅仅是法律所容认的“欺骗”,也要尽力杜绝,唯有如此才能让数字藏品行业长效、健康发展。
【参考资料】
1. 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三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2. 大判大正8·3·27刑录25辑第396页。
3. 陈少青,刑民界分视野下诈骗罪成立范围的实质认定,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285-304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22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60-61页。
5. 参见【3】,陈少青文,第 299页。